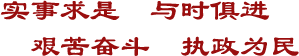黄少群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开始于1930年底,结束于1931年初,具体战斗时间仅5天,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和红一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本文不想对其战斗过程进行论述,只想就下列几个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蒋介石为何迟至1930年底才开始对“朱毛红军”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蒋介石自从投机孙中山革命成功和窃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并认为羽毛已丰以后,即举起屠刀,决心反共,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血腥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的北伐途中到1928年上半年,国民党蒋介石共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农、知识分子。此时蒋介石曾认为已经将共产党人杀戮殆尽,中国已经“彻底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了。朱毛红军崛起井冈山以后,蒋介石也只认为是“疥癣之疾”,不足为患,只命令江西军阀朱培德的部队去“剿灭”之;朱培德四次“进剿”不果,蒋介石也只命湖南军阀何键部加入,实行两省“会剿”井冈山。1928年底至1929年初的第三次“会剿”将朱毛红军赶下了井冈山“远窜闽西”以后,蒋介石又认为共军“残余”已不成气候,也只是命令各省军阀“严加防范”罢了。而在此期间,即从1928年6月起,他设法拉拢了桂、冯、阎三派军阀联合第二次“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由于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了不听话的张作霖,在艰难中“子承父业”的少帅张学良,面对蒋、桂、冯、阎四派军阀的强大军力,不得不实行“东北易帜”,归降国民党。蒋介石算是实现了他的“统一中国”的梦。
蒋介石本打算接着彻底“剿灭”红军。但随后却发生了长达两年接连不断的各省军阀们的反蒋战争。较大的如:1929年4月的蒋桂战争,5月和10月间的两次蒋冯战争,12月间的唐生智与石友三的联合反蒋战争,直至1930年4月开始的蒋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混战。中原大混战,双方调集100万军队,时间长达7个月,共50万人战死,无数人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其惨烈程度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正是接连不断的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才使得蒋介石无暇腾出手来“剿灭”红军。
1930年7月下旬,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袭占长沙城,接着红一军团奉命向南昌、九江进军。国民党报纸曾误传“共党占领南昌”。8月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7卷笫30期,以《共产党陷长沙南昌》为题报道说:“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袭占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这种惊惶失措的报道,使国民党朝野震动,蒋介石大为震惊。此时中原大战蒋军胜利已成定局。于是,8月5日,蒋介石即在河南前线匆匆忙忙密电南京政府先行筹划“剿匪”事宜,并准备抽调大兵南下“剿共”。10月10日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从郑州回师到上海,立即发表《告全国父老书》,提出“国家所最需求”的“刻不容缓”的“五项大事”,而将“肃清共匪”列为第一项。并具体任命了湘鄂赣各省区“剿匪”长官,“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
正是利用这个新军阀混战的空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特别是朱毛红军在此期间,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初步建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等到中原大混战结束,蒋介石积极部署对红军“围剿”时,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大发展,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
蒋介石为何将“剿共”总指挥何应钦换成了鲁涤平
何应钦与蒋介石早年都在日本学过军事。蒋介石随后任黄埔军校校长,何应钦则是军校少将总教官。何一向看不起蒋,蒋何矛盾贯穿始终。西安事事变时,任国民党军队代总司令的何应钦曾力主轰炸西安,企图乱中炸死蒋介石,以取蒋而代之,与汪精卫合作建立亲日政权。1930年8月间,蒋介石在前方密电南京政府,任命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湘鄂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先行筹划“剿匪”事宜。何应钦并不买账,竟复电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湘鄂赣剿匪事宜即由行营主任负责处理,似毋庸另设名义与机关,反滋纷扰。”即不同意另设“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的“名义与机关”,由“行营主任”何应钦直接“负责处理”即可。接着何应钦不请示蒋,而以“武汉行营主任”的身份两次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通过所谓《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15条,普遍布置“剿灭湘鄂赣三省大股匪共”。并规定“湘鄂赣三省现有驻军关于三省剿匪事宜,应悉听主任(即何应钦——笔者注)指挥之”。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即备文将会议内容及各种议决案文本呈报南京国民政府,以备批淮执行。
蒋介石对于何应钦一直有预防,一面想拉拢,一面在戒备。而对于何应钦的此次顶撞和自专,蒋介石更是甚感不满,心存芥蒂;且何应钦的方略是对湘鄂赣三省红军实行“全面会剿”,没有分出重点来,不符合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的主要意图是彻底“剿灭”“朱毛红军”。因此,不再想把“剿共”指挥大权交给何应钦。于是,10月28日,蒋介石也不与何应钦沟通,宣布另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并任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司令鲁涤平为行营主任,负责统一指挥这次“围剿”事宜,将何应钦晾在了一边。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到底派了多少兵
无论党史、军史过去都说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蒋介石“陆续调集10余万兵力”(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其实不然,按国民党战史记载应是“14万人”。
也就在发布成立南昌行营的同一天,蒋介石也同时发布了他拟定的“围剿”江西苏区红军的军事战略命令:“以歼灭朱毛彭黄及方志敏各股匪之目的,集结第六、第九、第十九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在赣境内四周包围各股匪于赣西地区及景德镇附近而歼灭之。所在赣之第五、第十八、第五十、新十三各师及独立十四旅及其他团队暂编为第九路军,统归总指挥(即鲁涤平——引者注)指挥。”蒋介石的命令发布以后,各军即奉调纷纷入赣。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6月出版、王多年的《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篇《剿匪》第一卷记述,具体计调军队有: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第二十四、第四十九、第五十六师及新编独立十四旅;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第五十、第七十七、第三十二师、新编第五、第十三师;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下辖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及独立第三十二旅和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另派三个航空队随时侦察红军行动,并支援地面部队之作战。以上计12个师3个旅,共约14万人。
笔者认为,写党史、军史,我方情况以我方资料为准,而敌方情况则应以敌方资料为准。这才大致能够做到不出差错。因此,笔者认为,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时派来的军队是“14万人”,而不是“10余万人”。
蒋介石还亲自为这次“围剿”制定了战略作战方针,即:“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具体计划是:三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向中央苏区进攻,在吉安、泰和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以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的袁水流域两岸地区,“聚而歼之”,一网打尽。蒋介石认为:先将红军主力“剿除”,“则其他股匪,不难摧陷廓清,盖即擒贼擒王之法也。”同时蒋介石还亲自悬赏5万大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等。
经过这一番部署,蒋介石认为以14万之众对付红军4万人,自可稳操胜券,一鼓而荡平“匪共之祸”了。于是,部署完毕,他将指挥大权交给了鲁涤平,自己则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陈布雷等游了一趟庐山,于12月26日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捷报”去了。他万万没有料到,最后等来的却是鲁涤平的一纸电文:“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还。”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中共中央对第一次反“围剿”发出了三次指示信
以往讲第一次反“围剿”,只讲毛泽东、朱德如何抵制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和对第一次反“围剿”的战略部署,不讲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后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党中央对第一次反“围剿”的指示。这是很片面的。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对第一次反“围剿”曾一连作出了三次指示,指导方略,通报敌情,倚重朱毛,指示各路红军服从朱毛统一指挥,悉听集中调动。可以说,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是经党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对第一次反“围剿”作出周密战略部署的。
1930年10月间,中共中央即已获悉国民党要向苏区和红军实行进攻了。为此,中共中央一连作出了三次指示。
第一次是10月29日,周恩来执笔起草和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给红军一、三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专门就对付敌军的第一次“围剿”的策略问题,作出了四点详细指示。
(1)一、三军团不要再为打长沙或南昌而争吵甚至发生分兵行动,“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一、三军团应坚持采取“进攻以击破敌人的策略”。“必须坚信:在敌人的进攻与‘围剿’中,在全国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能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只要我们能动员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反抗这一‘围剿’,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则胜利必将为我们所得。”
(2)“这次敌人‘围剿’红军的计划,是不限于一、三两集团军的所在地域,不过一、三集团军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因此,我们在反抗进攻红军冲破‘围剿’的中心任务下,必须使各地红军都能依照总的进攻策略,在各地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与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相互策应之效。这一原则,中央已具体化了指示红军,当着你们与其他红军发生联系时,亦应依此原则指导各部队。”
(3)不要“单纯以军阀战争的有无为革命发展之标准”,认为军阀混战“有了暂时的休息,革命发展便要受到挫折”,这个观点“完全是不正确的”。军阀混战发生,当然能“助长革命发展”,而军阀战争“一时停止了,也同样不能动摇革命高涨的生长”。“因此目前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军阀战争之暂时停止与否问题,而是要以开始的部分的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问题。要使革命战争能大规模发展起来,攻破敌人的‘围剿’这完全要看共产党运用的策略正确与否,及其发动群众的能力如何来判断,绝对不能归之于军阀战争之有无来判断的。”
(4)“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即项英——笔者注)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委员名单另附。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依中央上次通知,仍以朱德同志为一、三集团军总司令,当其他部队与中央区发生作战联系时,亦归一、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委暂不组织,俟江钧到后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集中到中央局。”
10月间,中共中央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进攻红军告民众书》,揭露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反动性,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劳动群众,“一致起来反对进攻红军”,“拥护红军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会议的政权”等。
第二次是12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专门作出《中央给红军的训令》。《训令》简要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主要精神,不仅对一、三集团军的“作战方略”作出了指示,而且要求各地红军都要配合一、三集团军的反“围剿”作战。《训令》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目前的政治形势与红军的总任务。训令分析了国民党进攻红军和苏区的必然性,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不是“占领进大城市”和“建立大的苏维埃根据地”,而是在现有的苏区内,“巩固自己的势力,必须最高限度的巩固红军的势力”,发动群众配合红军的行动,以扩大苏区和加强红军,来击破敌人的“围剿”。如果一味“企图夺取大城市”,则“完全是越过当前的实际任务,是冒险的盲动主义,这只有促成失败。”《训令》指出,只“要我们能坚决执行下面的条件,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已得的胜利,并且可以更加扩充苏维埃运动”。这些条件是:“A. 各地方党部,尤其是各苏区党部应当切实了解目前的伟大任务,是在组织反抗敌人的‘围剿’的运动,要能在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和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求解放的两口号之下来动员劳动群众,要切实在政治上组织上夺取广大的劳动者,正确的根据共产国际的训令,指导这些群众,使其在敌人向我方总进攻的现时条件下,为其阶级任务而斗争。B. 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者朱毛两同志在所有各级党部帮助之下,切实实行红军各部队的集中动作,并与农民辟众斗争相配合;并且我们不仅要在口头上,而且要在事实上,在军事以及政治上加强红军,使广大群众对红军有最高限度的援助。C. 要更加扩大在非苏维埃区域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工业中心的工人运动,并能正确的领导他们斗争。”
(2)红军的作战方略。《训令》指出:“现在反动统治阶级进攻红军的兵力,计算将调往和已调往的在十师以上,来与红军一、三集团军作战,企图消灭红军的主力”。“在现在斗争的紧急关头”,红军各部队必须采取下列的“作战方略”:“第一、三集团军在目前情况之下,应以赣南和赣东南为作战地区,而以闽粤赣为后方根据地。在这些地方,应该首先肃清该区内反革命势力和根源,同时务须击退敌人对该区的进攻部队。该两军团在防御时或由防御转为攻势时的兵力部署,须集中兵力于主要决战方面。极力避免分散兵力(放弃吉安的战况),否则会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能转为攻势而我后方与翼侧有戒备时,应突破敌军并消灭其部队。该两军团如获胜利而又为战况许可时,应当打通赣西以与湘鄂赣各部队会合发展;如失利而遭逢敌军重大压迫时,则可以闽粤赣为后方地区;如再不可能时,则可选择赣南或湖南为发展根据地,这须视实际情况来决定。”
《训令》接着对各地红军如何支援和配合中央苏区红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也都一一作了明确指示,并特别规定: “一、三军团及第十二军均在红军前敌总司令朱德同志及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直接统一指挥下行动,第七军(指从广西左右江转战而来的邓小平等领导的部队——笔者注)和第十军(指赣东北地区方志敏等领导的部队——笔者注)在与一、三军团取得联系后,必须立即听受其指挥。”
(3)在一般政治上和苏维埃组织方面的任务。《训令》主要就党和苏维埃的建设、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及红军给养,党和青年团的任务等方面作了一般性的指示。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涉,当时党在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上已经有了不少“左”的错误内容。当然,这个《训令》主要是关于反“围剿”的作战方略的指示,其他方面是附带提及的,而中央苏区和各大苏区又主要是在进行战争,所以这个《训令》在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的“左”的内容对各地的影响并不大。
第三次是在同一个《训令》中加的一个“附注”。原来,在11月28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项英)军委办事处发布一个文件:《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也主要是就第一次反“围剿”在战略问题上对红一、三军团和长江局所属湘鄂赣、鄂豫皖各地红军作出的指示。其中心内容不是为了集中兵力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而是要求各地红军配合红一、三军团来“取得占领湘鄂赣一省数省的胜利”,“以便依据军事政治条件来进占长沙或南昌”,并强调“各军行动配合的中心也在这里”。这依然是在继续贯彻李立三的“左”倾冒险方针。中共中央及时发觉了这个文件的严重错误。为此在上述《训令》的最后专门加了一个“附注”,明确指出:“最近十一月二十八日长江局军委办事处所发出的《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因有许多错误的地方,中央审查之后决定取消。”这就不但进一步廓清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也完全消除了红一、三军团和各地红军的顾虑,从而能集中力量来准备打破敌人的“围剿”。由此亦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和周恩来,对党的工作十分严肃和认真负责,对各地上报的文件报告,均都细加审阅和研究,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的三次指示,主要内容是:目前党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各苏区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以收到红军相互策应之效。对如何打破“围剿”,中共中央指示:要“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的三次指示信,对中央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是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的。
还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对前敌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十分信任和重视的,明确规定“红军各部队”均由“朱毛两同志”“集中动作”;各地红军一经“与一、三军团取得联系后,必须立即听受其(指朱德、毛泽东)指挥”。由此可知,中共中央是将打破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领导大任交给了朱德和毛泽东。
毛、朱是怎样抵制“左”倾错误,准备第一次反“围剿”的
从1930年6月至10月,朱德、毛泽东为抵制当时中央和红军中的“左”倾错误,争取回师中央根据地、准备第一次反“围剿”,四个月间可说是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般的艰苦历程。
1930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要求集中全国红军10万兵力,向武汉、长沙、南昌进攻,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大计划,并派涂振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专门到红一方面军中来传达贯彻中央计划,强行要求红一方面军立即向南昌、九江进攻,并严厉指出:“中央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口气咄咄逼人,丝毫不容犹豫!8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发布指示信,命令:“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对中共中央的这些硬性指示,毛泽东、朱德只得一面执行,一面在实践中寻找机会作了机智而巧妙的抵制。
6月,红一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7月间发布向南昌“推进”的命令。命令不用“进攻”而用“推进”,即只是将军队逐步向前“推移”,并不直接去进攻南昌。一个“推”字,体现了朱德、毛泽东的政治智慧。8日1日,红军在南昌城下牛行车站鸣枪示威,“纪念八一起义三周年”,随即向中央根据地回师。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会师,组成了红一方面军;接着按中央指示对长沙发动了历时16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决定回师根据地。但军中主要是三军团的一些领导人思想不通,坚持要执行中央指示,回师打长沙,甚至提到一、三军团分兵活动。在彭德怀的支持下,部队虽然东渡赣江,但一路却激烈争论不断。经过9月株洲会议和袁州会议,毛泽东耐心争取到长江局军事部长周以栗的支持,才决定回师打吉安。打下吉安后,与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再次发生打不打南昌、武汉的激烈争论。10月下旬在新余罗坊会议上,由于得到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特别是彭德怀等的有力支持,终于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红一方面军4万人回师中央根据地,实行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可知,从6月到10月,从撤围长沙到罗坊会议,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在存在严重争议的情况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作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