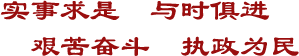孙启正 马贵杰
[摘 要]:“立三路线”之前,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遵循了“六大”确立的阶级路线。“立三路线”在鄂豫皖苏区贯彻后,主要表现为反富农和创办集体农场,但遭到地方苏维埃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沦为“口号”,背后隐现的是新式地方精英的“地方主义”观念。“立三路线”的纠正,在鄂豫皖苏区表现为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左”倾和反富农政策落到实处,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地方主义”最终被清除。[关键词]: 立三路线; 鄂豫皖苏区; 土地革命; 地方精英
与中央苏区相比,鄂豫皖苏区内,正式的苏维埃政权成立要晚一些,整个苏区存续时间也短了 2年左右。更关键的是,鄂豫皖苏区形成过程中,军队的行动是“跳跃式地行动”,而不是“波浪式地推进”,部队一走,“一切都塌台,地盘又落到敌人手里”。[1]地方工作、政权工作无法有序、坚实地展开,这对严重依赖政权建设的土地革命而言,尤为影响。民众对土地虽有热望,更存在顾虑。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权,分得的土地随时可能因地主豪绅的反攻倒算而丢掉,且民众付出的代价远不止归还土地那么简单。这也决定了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不可能如中央苏区那般广泛和深入。
鄂豫皖苏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精英的主导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浓厚地方主义观念。陈耀煌、黄文治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陈、黄二人接续西方学者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是由在大城市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回乡知识分子,利用其家庭、家族、地缘等关系动员民众而发动起来的。陈甚至认为,整个苏区时期,中共并未真正在鄂豫皖扎下根来,它的基础只及于新式地方精英———本地的苏维埃干部之上。笔者对此表示认同,本文的问题意识也正基于此。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受到“立三路线”影响时,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对“立三路线”反富农的普遍抵制和皖西、豫东南、鄂东北在响应举办集体农场号召中的差异性。联想到纠正“立三路线”时,不是以“右”的做法纠正其“左”,而是以更左的反富农“实践”纠正其“口号”。张国焘主政下的鄂豫皖得以将反富农政策落到实处的过程,恰恰伴随着其对本地干部的“整肃”。这些事实,也只有放在“鄂豫皖苏区革命的地方精英色彩”这一背景下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立三路线”前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
“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会议对土地政策作了若干原则规定,提出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用放手发动群众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会后不久,鄂豫皖边爆发武装起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也在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
暴动时期,共产党人对土地革命的范畴比较宽泛,但已初步意识到土地革命的意义。例如黄麻暴动之后,中共湖北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到,“中国革命,现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到处杀戮土豪劣绅,断绝水陆交通,破坏金融,抗租抗税,破坏一切交通机关,引起乡村间极大的骚动。”[2]48该报告中有湖北省对黄麻特委的一则关于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说到:“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分配土地的工作,非常重要,应看作比杀土劣更有意义”。[2]57黄麻暴动后短暂成立的黄安县农民政府,在其颁布的《黄安县农民政府施政纲领》中,即依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指示,提出要“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2]161不过,当时农民政府只是领导农民进行了没收豪绅地主财产、焚烧田契债票、开仓放粮等行动,尚无暇顾及土地问题。
黄麻暴动失败后,工农革命军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后在柴山保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28 年 7 月,鄂东党组织决定在根据地开展“五抗”斗争,同时没收地主、反动派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在没收、分配土地上,“根据群众情绪,采取了‘谁种的田归谁收去'”的简便做法。[2]107这是鄂豫皖苏区最早的土地分配方法。到 1928 年底,没收和分配土地只局限在鄂豫边根据地中心区域,其他地方由于战争频繁,根据地不稳定,未能分配土地。
1928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等三大决议案,基本上确立了一条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其中,对于富农的态度最为微妙,“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3]为后来“立三路线”时期富农政策的转向埋下伏笔。由于交通原因,“六大”决议于1928 年 12 月方才传达到鄂豫皖边区,其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规定为边区土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1929 年 5 月,鄂东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中小商人和富农问题》《公积祖积问题》等决议,作为土地革命的指导性文件。这几份决议的精神大致是:没收地主、豪绅、反革命的土地;富农的土地不没收,且有自由耕种权;公积祖积土地归苏维埃处理。可见,这时对富农的态度比“六大”还要温和。《临时土地政纲》等颁布后,鄂豫边根据地从 1929 年 6 月至 12 月,黄安县的七里、紫云、桃花、仙居,麻城县的乘马、顺河区,光山县的柴山保、观音保、官堰保,商城的合区、乐区,新县南乡的箭河、田铺、泗店等地完成了没收与分配土地。[4]1929 年 11 月下旬,鄂豫边根据地召开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决议案反映出对富农政策摇摆甚至不无矛盾之处。如《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以雇农为主要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 《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则指出,“以后绝对禁止富农入党”。 但在《群众运动决议案》中则规定,要根据斗争形势决定对富农的态度,大体上,在开始斗争的地方仍旧政治上中立富农,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对富农的剥削采取减租减息;在斗争发展的地方(苏维埃区域),则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分配富农剩余土地,将反动富农视同地主一样处治。1929 年 12 月下旬,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制定的《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是对《临时土地政纲》的细化,对富农的态度,原则并未改变,只细微调整为“凡富农愿将土地拨归公者,当地乡农会得接受分配之”,仍旧较为温和。于是,鄂豫边的富农政策就呈现为“政治上反对,经济上照顾”的奇怪局面。
1929 年是苏联集体化的关键一年,大批富农被清洗或流放,这也标志着苏共内部斯大林对布哈林派斗争的胜利。在这一背景影响下,布哈林主政共产国际时期帮助中共制定的富农政策(“六大”决议案)面临调整。1929 年 6 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国共产党,指出“在政治决议上之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词句……可以使人在解释六次大会之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时候,以为这是因为不要摇动富农的财产,其实这是不正确的。”[5]694经过讨论,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决议接受国际指示。对富农政策从“六大”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富农,转变为“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5]454可见,早在鄂豫边根据地之前几个月,中共中央的富农政策已经“左”转。
当然,各地苏维埃接受中央决议有滞后性,我们不知道鄂豫边区最早接收上述中央决议的确切时间。有据可考的是,最迟在 1929 年底,先是曹大骏受中央派遣,到鄂豫边界成立特委,随后才有鄂豫边根据地第一次全区代表会议的召开,再接着 1930 年初,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曹大骏回到上海中央。亦即:曹大骏全程参与了鄂豫边特委和革委会一系列决议的制定,但并未使以地方干部为主导的鄂豫边根据地完全根据中央意志转变富农政策。曹大骏回到中央汇报工作后不久,中央即发出指示信,指出鄂豫皖边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路线非常的严重”。[6]至此,鄂豫皖苏区对中央指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富农政策的转向采取消极抵制,已是显而易见。
二、“立三路线”时期鄂豫皖的反富农与“集体农庄”
“立三路线”的形成有个过程,一些提法甚至可以直接在“六大”相关决议中找到依据。比如《政治决议案》中“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提法就源自共产国际的意志,当时就被瞿秋白作为替“盲动路线”辩护的说辞。“立三路线”后来援用了这一提法;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六大”上不主张过分强调反富农,也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有所体现。但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苏共内部正在发生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斗争,李立三认定苏共正在反右倾,布哈林即将失势。因此,他曾向张国焘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大林一面,……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7]388 - 389“六大”结束后,李立三回国先后担任农民委员会书记,中央宣传部长,“立三路线”开始形成。“立三路线”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富农政策的极速“左”转和集体农场(庄)的创办。
1930 年 3 月,中央代表郭树勋、曹大骏、许继慎三人来到鄂豫边特委,纠正边区党的富农路线作为任务之一。同年 6 月,鄂豫皖边特委在光山县王家湾召开了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 了 鄂 豫 皖 边 区 苏 维 埃 政 府,甘 元 景 担 任 主席。[8]6 月下旬,鄂豫皖边特委在黄安县莲花背召开会议,会上除了赞同中央关于反富农的路线外,还通过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决议。此外,会议还决定派王平章到皖西地区去执行中央关于反富农路线的指示。
在 1930 年 3 月中央指斥鄂豫皖边根据地充斥着富农路线的同时,湖北省委也被指责“最严重的问题是富农路线问题,各种错误都是由于富农路线”“在红军、农协中有富农领导,党内也有富农,苏维埃有富农。我们的同志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有富农思想,仅仅驱除富农分子,不改变富农路线。我们一定要在党内、农协内、苏维埃区域反对富农路线,要坚决的加增雇农工资,组织雇农向外发展,加重富农负担。不论是什么人,如果有富农思想,都要坚决反对。这并不是枪毙一切富农,只有他服从我们的法令,如果他反对,那就要枪毙”。
可见,“立三路线”认为,之所以要加紧反富农,是由于富农混入党内,阻碍了土地革命等政策实行。这种指责,并非无的放矢。实际上,早期鄂豫皖苏区的发展过程中,地方精英占了极重要的地位。据中共黄安籍党员郑位三日后的回忆,早期在黄安活动的共产党员,多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9]。当时的中央巡视员何玉琳也曾指出,在鄂东北区的党中,“愈上级愈多学生分子”。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多是富有的地方精英家庭出身,也只有这些人才有能力当学生和知识分子,一般的下层贫苦工农是没有这种能力的。据 1930 年初的统计,在六安中心县委中有 75% 的党员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党员中有 25% 是在家中吃租课过活的。由于苏区的党是掌握在少数地方精英的手中,这些地方精英又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因此,除部分来自中央的代表以及少数理想信念坚定的地方精英党员外,深入土地革命和坚决反富农的决议很难得到完全的支持。据黄文治研究,1930 年上半年,反富农政策是在从上而下地传达,但大规模反富农政策并未得到强力推展和落实。主要原因“是传达反富农精神的中央特派员之后即回上海,而颇多富农出身的地方精英党员则采取了隐性抵制的‘反行为'”。[10]
实际上,早在 1929 年底郭树勋在鄂豫边根据地传达中央的反富农政策时,本地干部徐朋人与戴季英等人即表示异议,徐还因此被撤销鄂豫边特委书记,改任组织部长。新任特委书记郭树勋前往黄安开会时,黄安县委书记戴季英避而不见,在郭离开后“又另开(会)”[11]。另外,诚如陈耀煌所言,苏区的下层群众并未形成对共产党确切的认识与深刻的阶级觉悟,这就使“立三路线”的反富农停留在“自上而下”机械执行的阶段。1930 年下半年,鄂豫皖边区的反富农也未走上群众路线,反而形成少数苏维埃委员与土地委员的包办。在鄂东北地区,“执行反富农策略没有发动广大群众的行动,而形成了机关的反富农与少数同志的反富农”。 据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革委会成立后黄麻地区土地虽得到彻底分配,但分配过程中由于“富农意识的笼罩(苏维埃或农委会以大部分是富农分子),及封建感情的冲动”,土地分配未能全盘得到正确的解决。“有感情式的分配,有吃鸡式的分配。(党员吃了农民鸡肉,就把肥的土地分给他)。……富农剩余土地,有用政权强迫分配的,有的用政权去袒护他而责斥农民左倾的。”[12]曾中生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有些负责分子是感情作用,于是富农分子没有受到这些压迫”。 可见,由于鄂豫皖苏区干部多系地富家庭出身,在执行中央反富农政策时,照顾、迁就富农的现象并不少见。“立三路线”后期,以累进税的形式征发富农财产代替对富农的政治打击,以至于“向富农征发代替了全部反富农斗争”。这意味着中央与地方精英出身的干部在富农政策上达成了一定的妥协。
“立三路线”在经济上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号召各根据地建立“集体农场”。1930 年 5 月 15 日,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刊出。该文是李立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的合辑,集中体现了“立三路线”的主张。李立三判断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面前。”因此,“必然同时提出的就是革命转变———从民 主 革 命 转 变 到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的 问题”。[13]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模仿苏联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场(庄)。鄂豫皖苏区执行这一号召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鄂豫边特委在中央的鞭策之下在中心苏区黄安有过实践。
据袁克服建国后回忆,在“立三路线”影响下,鄂豫皖特委于 1930 年 10 月,决定在黄安打造集体农场。当年割谷之后,在黄安十个区中的八个区筹备建立集体农场,最热闹的是三区和四区,“上级决定在长冲、七里坪创造两个模范农场。长冲农场成立时集合四十余工人,十九条大牛、150 余亩土地,当地农民全部迁往旁处安插。农场内工会领导各生产小组,支部只起保证作用。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生活紧张,要上操识字。”四中全会后,结束了“立三路线”,农场也就在当年春季结束了。“该农场历时三个来月,钱花费好几千,做的事情就是捡了点柴,弄了些粪。解散时钱与粮食给了机关,粪给了老百姓,三一年春季结束,旧历新年的正月十五,工人才走完。”
而在豫东南地区,由于“受到广大干群的抵制,光山、罗山、商城等县均未开办”。[14]皖西地区,六安中心县委虽在 1930 年 7 月初召开的六安、霍山两县党的联席会上,确定了一条“坚决反富农”的阶级路线。但“六安中心县委对反富农政策有怀疑,执行不积极,并迅即在七月中旬召开的四县( 六安、英山、霍山、霍邱) 联席会议上作了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时间短,在皖西还不到三个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时,就基本停止执行。”[15]亦即,皖西连“立三路线”的反富农路线也未实践,更遑论办“集体农场”了。
总而言之,“立三路线”的两个主要土地政策,一是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从“不要故意加紧反富农”转为“坚决反富农”;二是号召创办集体农场,在鄂豫皖苏区均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无论是对反富农政策的阳奉阴违,刻意架空,还是响应集体农场号召时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三块根据地的差异性应对,均足以证明鄂豫皖苏区仍是一块充斥着地方主义观念的以新式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根据地。
三、“立三路线”的终结与鄂豫皖地方主义的消除
“立三路线”除在国内掀起革命高潮外,还要求“国际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注意中国革命问题,准备拥护中国革命伟大的斗争”。[13]据时在苏联的张国焘回忆,共产国际对李立三要求外蒙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蒙以配合中国革命的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7]441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于 1930 年 9 月 24 日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立三路线”。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中,表示“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5]14但这次会议的精神是调和主义的,李立三、瞿秋白仍控制中央,“立三路线”的影响仍在。共产国际遂采取进一步措施,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去,一面准备通过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彻底解决肃清“立三路线”。1931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由向忠发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要求党内要从“理论上实际上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错误。”[5]18会上通过了《四中全会决议案》,反倒指责李立三过去有“联合富农的理论”,所提议的“集体农庄及一切过早的社会主义办法,事实上不能不使富农地位反而更加巩固”。[5]19这就为鄂豫皖苏区用更左的办法清除“立三路线”奠定了基调。
1931 年 4 月初,张国焘受中央委派来到鄂豫皖苏区,5 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如上所述,对“立三路线”的纠正主要体现在军事、政治上,在土地问题上乃是以更激进的土地革命路线来代替“立三路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推行中央的“左”土地政策中,更是变本加厉。对此,分局主持制定了两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一是《反对富农问题》,一是《关于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材料》。前一个文件将富农定位为“农村中的剥削者”,并且“反富农是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政权机关“已有的富农分子立即由政府和群众清除出去”,经济上则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必要时“征发” 其粮食,没收其“多余的牛和耕具、房子”。《关于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材料》的主要内容是鄂豫皖根据地为什么要重新分配土地及其分配办法。该文件指责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和鄂豫皖边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颁布的《土地政纲细则》及《土地暂行法》“犯了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致使“鄂豫皖苏区的土地虽经过几次的分配,但……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从而事实上全盘否定了前期土地革命的成绩。这两个文件所体现的,正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革命路线。其实行的结果,则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
张国焘作为中央委派的外来干部,其意志时时受到带有浓厚地方观念的新式地方精英的挑战,亟待通过清除地方主义,确立自身权威。因此,通过将土地革命路线“左”倾化,借以打击多系地、富出身的本地干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正如黄文治所分析,“张国焘等来鄂豫皖苏区反富农,既有民中再动员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需要,同时亦有借反富农加强该苏区控制权的成分,而两者的实现与显效亦相得益彰。”[10]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形成的“左”倾的土地政策,恰好与张国焘整肃桀骜不驯的地方干部的现实需要相符合。1931 年 10 月,正值鄂豫皖的肃反“白热化”之际,鄂豫皖中央分局致信各地方,明确指出肃反主要是“淘汰异己分子”,而“异己分子的内容主要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此一指示使张国焘借土地革命反富农之名,行整治不服从的地方精英之实的“策略”昭然若揭。自此,在土地革命中以发动群众的形式在经济上削弱富农,政治上打击富农与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杂糅在一起,从而基本上扫清了地方主义观念,重新形塑了鄂豫皖苏区党的内部风气。
四、结语
纵观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的历史,新式地方精英以及该地区由来已久的地方主义观念始终穿插其间,与来自中央的路线和外来势力龃龉与调适。出身地、富的苏维埃干部,作为新式地方精英对土地革命始终未能完全接受和全力推动,使“立三路线”及其之前的反富农政策被化解或架空,阻碍了土地革命的深入推进。张国焘主政之后,借“左”倾土地革命路线整肃地方精英,虽将土地革命推展至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深度,但在以此消除了地方主义的同时,事实上也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在该地区的根基。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苏区,提前“长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12 -113.
[2] 红安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黄麻起义[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3] 中央档案馆,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56.
[4] 谭克绳,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1.
[5] 中央档案馆,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96.
[7] 张国焘. 我的回忆(2)[M].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 1980.
[8]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4)[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73.
[9] 郑位三. 红色的黄安[J]. 党史天地,2007(11):25 - 28.
[10] 黄文治. 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实践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1.
[1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中共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上)[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916.
[12] 湖北省档案馆,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488.
[13] 李立三.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J]. 红藏·布尔塞维克,1930(3):377 - 398.
[14] 董雷,刘心铭. 豫南革命史[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53.
[15] 陈忠贞. 皖西革命史[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