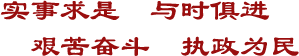[摘要] 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由南向北进行了大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经过艰苦的牺牲奋斗,将为求生存被动进行的转移,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主动进攻,并胜利地实现了革命中心的北移。而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成为各路红军这次胜利转移的最终落脚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由陕甘根据地扩大而成的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和出发点。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由南向北进行了大转移。转移的原因,起初是因为在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的强力“围剿”下,由于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南方各红色根据地丧失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正确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经过艰苦的奋斗,将为求生存被动进行的转移,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主动进攻,并胜利地实现了革命中心的北移。而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成为各路红军这次胜利转移的最终落脚点,同时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出发点。
一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来,中国革命的中心一直是在南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以及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都是以南方为中心逐步展开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中心摆在了中国南方。南昌起义后向广东的进军、海陆丰的武装暴动和广州起义,以及稍后的广西百色起义,都有先建立两广根据地,再度北伐的意图;毛泽东也认为,红军的组成、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区,必须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当时先后建立的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和陕北之外,基本上都分布于中国的南方省份。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中国革命的中心逐步由南方向北方转移。这表现在:
其一,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来,北方长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但是,清末以来,继清朝封建统治的覆亡,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及其随后在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的土崩瓦解,在中国北方,不仅旧的反动统治势力已经被摧毁,而且继之而起的新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势力,也在新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的过程中遭到沉重打击。北方反动统治力量大为削弱。
其二,大革命后期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的蒋介石政权,由于得到江浙等富庶地区地主买办阶级以及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1928年12月,随着东北易帜而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接着,南京政权在与各路军阀混战中,一一胜出。特别是在中原大战中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以及消除汪精卫等国民党内各反蒋政治派系的联合挑战后,其统治力得到空前的巩固和膨胀。虽然此后直至蒋介石政权最后在大陆覆灭,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甚至是武装磨擦一直没有停止过,但都已不足以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其三,在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平息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在其统治的中心区发动更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使长期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共中央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与此同时,他还纠集武装力量对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各路红军和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在强敌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各红色根据地最终难以支撑,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其四,“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热河的武装侵占和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渗透,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出现和绥远抗战的爆发,以及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酝酿,表明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新的革命高潮正在中国的北方日益高涨。
而位于北方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北),硕果仅存,历史性地成为党中央与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新的革命高潮的策源地。
二
进行战略转移的各路红军最终需要有一个落脚点,所以,能否重建新的根据地成为长征胜负的标志。这是红军将领和党的领袖们的最终共识。当年刚刚抵达陕北瓦窑堡的毛泽东,就曾明确地指出:“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豪迈地宣告: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中各路红军长途跋涉寻找或开辟新的根据地的过程,恰恰就是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过程。
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各路红军都曾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其中,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师后,曾建立了以湖南大庸(今张家界)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月到11月);红四方面军则建立了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10月到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这三路红军一度或部分取得成功的原因,除去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注重发动群众,以及分别有贺龙部队、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鄂豫陕地方党组织接应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上述地区在红军开进时尚没有蒋介石的嫡系武装进驻,而当地的军阀又分为多个派系,利益纷争。随着国民党正规军的跟进,特别是在蒋介石以中央政权的政令统一指挥调度和严厉督促下,地方军阀协调一致共同对我的情况下,这三支红军虽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已经很难再站稳脚跟,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后来,红四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的电令,红二十五军则是依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和战场形势,分别决定并陆续重新踏上长征路。这反映出南方地区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红军已经难以在那些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中国南方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在中央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中央红军作为红军的主力,又是和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起行动,更成为敌军疯狂围追堵截的重点。在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八万多红军锐减为三万,伤亡重大,这使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成为泡影。
毛泽东洞察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转兵贵州的意见,经过在老山界的争论和通道会议的讨论,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当时还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作为新的进军目标。
遵义会议后,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又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但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的失利,又迫使中央红军于29日拂晓前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2月3日至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叙永石厢子的万寿宫(当时属古蔺)开会,决定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避开敌人锋芒,准备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从而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并确定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
这一时期,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与强敌周旋。他根据敌情变化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往哪个方向进军的问题,急需作出抉择。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这首先是基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边的敌情和相关战略方向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当时夹金山以南是国民党的追兵严阵以待,向东岷江、成都方向也有130个团重兵把守,向西则是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向北经川西北到川陕甘地区,那里地势开阔,人口稠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其次,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据地努力的落空等残酷现实,使在中国南部敌强我弱的大环境短时间很难改变,即使是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也会在强敌的持续围攻下难以为继,还必须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与支持。靠近与中国西北等地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正如毛泽东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的,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这样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因此,进军川陕甘的战略发展方针是当时唯一可行、后来又被实践证明的正确方针。
后来,毛泽东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调整。1935年9月28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从报纸上进一步了解到的陕甘苏区状况和红二十五军已经与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这一新情况(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到中央苏区参加了“二苏大”的贾拓夫,长征中以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身份一直随中央纵队行军,他已经介绍过陕甘根据地1932年10月以前的一些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
三
陕甘根据地(包括陕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来时,已在连成一片的20多个县(一说23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所及达30多个县,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这里有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4000多人,另有相应人数的游击队,加上新近抵达的红二十五军,陕甘根据地共有红军8000人,与陕甘支队的人数大体相当;这里临近抗日前线,又与苏联遥相呼应,符合实施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打通国际线依托苏联、发动民族抗战推动革命新高潮战略的条件;这里虽然也被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以及宁夏马鸿逵等军阀武装所包围,但由于这些地方实力派同时还与蒋介石之间心怀二志,客观上对蒋介石嫡系追兵的“进剿”起着束缚手脚的作用,这使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稍得喘息;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人口150余万,长时期以来受到共产党人的发动和影响,特别是多数地区已经进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群众的斗争觉悟普遍很高,并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骨干和干部队伍。但是在另一方面,陕甘根据地客观上也存在着与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新的革命高潮策源地这一重要地位不相称的差距。这主要是地域狭小、地瘠人贫,特别是在中央红军抵达这里时,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开展的肃反运动,使包括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在内的一大批领导人和红军骨干被抓、甚至被杀,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如何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党中央抵达陕北后萦绕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脑际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认真反思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丢失中央根据地的原因。他认为:“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指中共与外界的交往,而不是专指与外国的交往——引者注)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有鉴于此,毛泽东主要从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三个方面领导进行了巩固与发展陕甘根据地、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艰苦努力。
第一,开始全面地纠正受“左”倾错误影响的组织路线,首先是果断地停止了在陕甘根据地进行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同时,给予在陕北搞肃反者以处分,改派李富春为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书记。当听说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9页。)鉴于因为肃反造成的红十五军团内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之间的隔阂,他要求对红二十五军和由红一军团调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干部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对陕甘红军“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对陕甘红军干部中“尚怀不安与不满进行诚恳的解释”,“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1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应该“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武装力量出发”予以重视。他要求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同时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11页。)他在给红军主要将领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0—501页。)
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遵义会议前后就已开始着手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江西遭到撤职和错误批判的邓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通过调整中央分工,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人受到撤职处分。一些甚至是在保卫局监督下参加长征的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战斗岗位。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的要职;再如凯丰,到延安后仍让他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对于张国焘,毛泽东更是苦口婆心。由于树立和贯彻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错误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转移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第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以陕甘根据地为依托,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还用很大的精力总结自己的军事思想,力图从理论上肃清“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并以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军。他在保安(今志丹县)创办了著名的窑洞大学——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并亲自为学员们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彻底肃清。
第三,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尚有异议。当时王明等“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具有很大影响。他们根据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在强敌的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无独有偶,在陕甘根据地主持肃反的北方局代表也不切实际地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线。(参见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甘肃文史资料》第9期。)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伊始就打出的旗帜。1934年7月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到闽浙赣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提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北上抗日,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抉择是,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问题,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是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提出更切实可行的主张。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7页。)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大团结、共御外侮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此后,毛泽东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指挥红军予以坚决打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致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立足于陕甘根据地,努力扩大红军,积极发展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提出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以西北的联合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重要战略。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客观上成为发生西安事变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由陕甘根据地扩大而成的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和出发点。
长期以来坊间流传着两句话:究竟是陕甘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甘?从上述情况看,没有陕甘根据地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到来,陕甘根据地也难以为继,更不会有后来的辉煌与影响力。1945年4月,在长征胜利十年之后,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这样评价陕甘根据地:“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他的话,一语中的。〔作者蒋建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